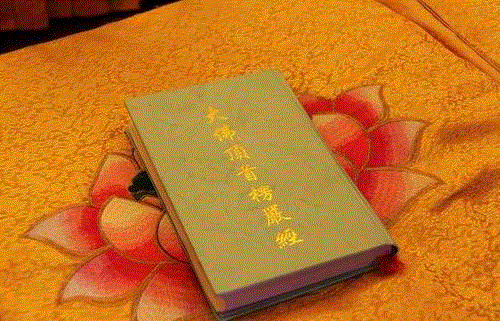一位耶鲁佛学博士的佛学研究之路(四)
发布时间:2023-09-11 02:35:38作者:楞严经全文网
来源:http://manyuer.bokee.com 作者: 王翔
三、当泪水滚落(中)
当孤独嘹亮的号声划破晨曦初放的天空,吸满晨光的厚云低低下垂,远处响起呼唤我名字的尖锐声音要我为荣誉奋斗时,我必须一跃而起,独自启程。
——三岛由纪夫:《午后曳航》
这期间我也从北京的西面搬到了离北大比较近的小南庄,成了一个房客。窗外来往的是滚滚的车流,房东是一个经营着数个房客生意的老太太,老人家年轻时代经历过抗战,对日本人苦大仇深,她的兄弟曾经参加过解放战争,现在的不幸是她的女儿患了白血病,想来生活也不容易。这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老太太,就这样挣扎着活到现在,眼睛虽然看不清了,但是性情依然火爆。她养了两只猫和一只狗解闷,我也常常和它们玩,夏天的时候,豆豆(狗的名字)就跑到我的门缝这里趴下,吹吹空调。而那两只特立独行的猫却和我不甚友好,估计是因为我在,他们不能常常到我的屋子里来趴在床下了。这个时候我的伙食基本就是楼下某个单位的川味盒饭,价廉物美,味道不赖。有的时候也去北大吃饭。重新感受做一个学生的滋味,多少年来,我一直这样热爱着北大,她的四季风物,百花齐放的文化气氛,热闹多彩的学生生活,永远让人怀念。
因为当时想要学习艺术史,我就去旁听朱青生先生的课程,在他的周围的确实团结了一批有志于学,颇有才华的青年,他们分布在各个科系。所以上这种课,就像一个工作组在钻研一个课题,也是不分南腔北调,百家争鸣。就我现在所知的(2003/4)有去西北大学学习艺术史的,有去康奈尔学习电影批评的,还有今年要去斯坦福学习语言学的,另有几位也是我非常看好的高手,加上我这个要去学习宗教学的,可见这个小团体真的是精英辈出。这个时候我认识了S,因为这也涉及她的隐私,所以我也不能细谈。2001年的我真的很投入去恋爱,可是这次的事情太过于极端,越过了很多难以承受的极端,让我幻灭到了准备彻底觉悟的地步,想起在耶鲁最早的日子,一边是沉重压力的功课,一边是无边的悲伤,致使我的肺部都出现了问题,真正地体会到了“痛彻心扉”的滋味。现在想来,我的所谓的“爱情”经历都是悲剧吧,不过只有彻底的悲剧才能让你认真的思考人生的无可避免的无常,体会到生命的痛苦。那是2001年的独自度过的寒冬,我出没于宏伟的Sterling图书馆,在14层的大书库中徘徊。寒假大家都走的时候,雪冷风清,我一个人留连于第12层的佛学书架前,我觉得当时是李元松先生的书救了我,他写的那几本书我都一一借走拜读。但是我借走的时候从不会想过这不仅让我看到了解放的希望,而且转变了我的求学方向,就此走向了佛学和宗教学的海洋,尽管此后有过了近2年多,我才有攻读佛学博士的机会。我同时借回来的还有张澄基的《佛学今诠》。
飞到美国的那一天首先是在晨光初现的时候看到加州的海岸,然后是洛杉矶机场的等待和飞向黑暗的纽约的旅程。在疲劳中迎接了东部的夜晚,不断的一个个城市组成的巨大光源在飞机下呈现,直到纽约进入视野。那时候正好下雨,我坐在机窗前,看见机翼高速地穿行在夜色的雨雾中。一群人到达耶鲁的时候是凌晨了,随便找了间屋子就睡着了,接下来是繁忙和新鲜的几天,不过夜晚来临的时候, 非常安静,我会听坂本龙一的Forbidden Cloud, 悲伤而又优美的曲子,在遥远的他乡,在悲愤而无处倾诉的心里激起特殊的感觉,这些音乐加上后来不断下载的和平之月的曲子,我这第一年听的都是慷慨悲凉或者宁静悠远的音乐。
耶鲁的生涯其实充满了波折和艰辛,回想起来应该是目前工作量最大的两年,改变非常大,基本上树立了我的学术方向,极大地锻炼了我的研究能力和学术眼界,可以说是我迈入学术大门的第一步。第一个学期我不知天高地厚,选修了三位名教授的课,History of Traditional China to 1600 (instructor: Prof. Valerie Hansen韩森) 1600年前的中国古代史,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 instructor: Prof. Jonathan Spence史景迁) 清朝和民国,Man and Nature in Chinese poetry (instructor: Prof. Chang Sun Kang-i 孙康宜) 中国诗歌中的人与自然。但是我对耶鲁高标准的学术没有什么了解,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很多材料应该保留下来。(所有的课程请参看耶鲁和港大的课程)有些课程如果让我重上,我会有更大的收获。这个学期真的非常艰苦,我盼望着冬天的到来,在我最悲痛的时候,我还要为课程而完成paper, Valerie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高我一届的北大历史系毕业的小薇就曾经在图书馆中因为学习过于用功而昏倒过两次。她的课程视野也颇为新颖,采用了很多考古材料。我被要求重写论文,本来我是比较各朝代的都城,但是最后我只能改写唐宋元的妓女,不过这是我真正地接触各种古典文献的第一步。史景迁这样的大牌教授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受益匪浅,他的课程广泛地谈论了各种历史课题,包括八旗、萨满教、人口和环境问题、清代的鼠疫、民国时期的共产党,上海的妓女问题、思想史的问题等等。这个学期的困难刚才已经阐述,我急切地盼望着寒假的到来,能够安静地看看书,思考一下。这个风雪弥漫的冬天彻底的改变了我的学习方向,我开始进入了佛学的这个领域(Buddhist studies),才渐渐地发现它的广阔依然出乎了我的想象。
第二个学期来临的时候,我一开始选择了四门课,因为我尚没有下定决心学习佛教,所以并没有选择Silk教授的印度佛教(后来在港大读到Silk 教授编的藏英对照的三部大乘经典,回忆起这个细节),Silk 教授后来前往佛学研究最盛的UCLA,加上它们原来就有的四个教授,使得洛杉矶分校成为全美佛学研究最强盛的地区。我选的课程包括了禅宗和欧亚大陆的艺术,分别是日本佛学专家Paul Groner和圣彼得堡博物馆的Boris Marshak主讲,特别是Marshak的讲座极具水准,精彩纷呈,涉及到古代近东、中亚,到中国北方的多种文化和语言。这门课在古雅的耶鲁博物馆内的艺术史系的教室里上,我常常在那城堡一般的走廊里等待上课,看着一楼的大理石雕塑。可是后来我觉得这么多课程的要求太高,加之我需要时间思考和学习对自己的精神更有帮助的课程,我就将这门课转为选修。这时候的心态也使我对美国的学术表示了怀疑(参看给康正果老师的信 2002/01/12)。放弃了生物学博士前途的马蒂厄在“和尚与哲学家——佛教与西方思想”这本书中,面对他的父亲让—弗朗索瓦的询问,也同样提出了他对于人文研究的疑惑:
“在我成长的环境中,由于你,我遇到一些哲学家、思想家、戏剧家;由于我的母亲,画家雅娜·勒图默兰,我遇到一些艺术家和诗人……例如安德烈·布勒东(Andre Breton);由于我的舅父雅克—伊夫·勒图默兰,我遇到一些著名的探险者;由于弗朗索瓦·雅科布,我遇到一些来巴斯德学院举行讲座的大学者。我就这样被引导着与很多方面的有慑服力的人物相交往。但是,在同时,他们在自己的学科中显露出的才华并没有必然引起这样一种东西,我们称这种东西是……人的完善(Perfection humaine)。他们的才能、他们的知识和技艺的能力并不因此就使他们成为好的人类存在者。一个伟大的诗人可能是一个骗子;一个伟大的学者,就他自身而言,可能是个不幸的人;一个艺术家,则骄傲自大。所有的或好或坏的结合,都是可能的。

这个学期我的重头放在禅宗的学习,它真正地开阔了我的眼界,但是其实这时候我在这一领域的知识是严重不够的,我因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在上交的paper 上遇到了打击,Groner教授认为这篇文章has no sense of history, 他说我应该系统地学习佛教,我因之而无法得到他的推荐信,当时我迈出他的办公室,往图书馆走去,虽然是个晴朗的日子,却不知道未来该往哪里去。其实现在 (两年之后)看起来,当时的水平确实是不够的,也无怪乎教授不满意。这个学期我认真地思考了从艺术史转向佛学研究的问题,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而且耶鲁的局面是这两个领域的教授都退休了,我暂时无人可以从学。可是在学期结束的时候,追求解脱道的精神还是激励了我去选择佛学。
这个迷乱的假期有很大的一段时间是在西藏和四川度过,我希望寻找自己的伴侣,却不知道她在那里。国内喧嚣的气氛让很多人都感到茫然,沉下心来想想会觉得生命建立在那些镜花水月的东西上,如同沙造的城堡。第三个学期为了申请的考虑,我准备多多选修语言课程,我一开始选了日语、法文和梵文,后来发现梵文课的主讲是Stanley Insler——伟大的哈佛耶鲁梵学体系的最后一人,我同时要跟上三门课程是不可能的任务,最终选修了法文和日文。这一年的课程是我最累的一年,每个学期四门课,其中包括了天天都要上的语言课,听说读写,一应俱全,还要作申请。很多的时候,在孤独中我忙到凌晨了居然连作业都没做完,有时候听着日语的录音居然就睡着了。在寒冷的清晨,我必须早起,穿过数个街道,走到如同城堡一般的教室中去,下雪的时候我望着old campus的dormitory,和童话故事中的建筑没有什么两样。这其中我选修的比较有意思的课程是religion and rebellion in East Asia以及Understanding Buddhist sutra, 随着知识的深入,我对于做研究也有了概念,加上自己的经验对于其中的甘苦也更有了解。对一个领域的知识经过不断的量的积累,会终于在某一个阶段达到豁然贯通的理解。
抗战不过8年,在美国攻读人文博士,漫长而又艰苦的事业(我在更新中有多处谈到这一点),在全球跋涉7-10年,学习2-5种语言是常有的事情。只是为了学位已经不足以支撑漫长的求学生涯。想要学有所成的人到了后来,所学的如果不是真正安身立命的学问,如果缺乏着了迷一般的激情,在学术和内心中恐怕也不会得到安宁。我所见到的固然有苦苦坚持的人,也有相当纯粹地追求真理的学人。他们投入全部的身心,日日在图书馆中读到晓星初上。因为,在我看来就是,他们在这样一流的但却是“非人的”学术训练中承受了各自不同的牺牲,日积月累就成了精神和肉体一起加入的全面的奋战。到目前为止,我最累的两年就是耶鲁的这两年,而如今又深入一个不同的专业领域,在未来所面临的挑战更是惊人。在这个过程中我渐渐地远离了喧嚣的世俗,以超越今生的角度来看,我们对外物名声的追求终于会尘埃落定,对于读书破万卷,文科学习已达9年的人来说,充满了sound and fury的生活已经没有太多的意义,厌倦了不断挣扎于灵肉之间的人世,抛却了许多世间所沿袭的观念,连光耀门庭的心态也早已平息,活着只是为了逼近精神的解放和终极的真理(哈佛的校训不也是说,最重要的是要以真理为友)。但是自己做出这个选择历经了10年的荆棘之路吧。这期间也要忍受常人难以逾越的孤独和寂寞,寒来暑往,学业在进步,心态慢慢地老去。节日来临的时候,也常常是一人而已。复活节来临的时候,我们这样的外国学生交5美金就可以去吃一顿火鸡宴,记得那时路上已经没有什么人,我们算是体会到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滋味。每个留学生都很忙,相互的距离似乎从开始到结束都差不多。我很有幸和刘启后谈的来,在那耶鲁的第二年里,我常常和他一起喝酒闲聊,一抒胸中之气。
很显然,这第二次的申请在极度的繁忙中度过,因为准备不够所以申请得很不理想。虽然得到了UIUC的offer却有数千美金的缺口,申请的时候真的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想告诉那些准备学习文科的朋友,挫折和大起大落常常难免,我遇到的很多博士走的都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在很多关键的时刻需要毅力和拼搏,这一点就如同奥林匹克的比赛一样,在申请之中,最关键的还是你的背景和实力。这三年来我感觉个人的精力,运气高扬的斗志是如此的有限,将全副精力集中于此始有成就学业的可能,尽管会有波折和无常,我依然愿意相信这一天应该会来临。我所观察的世界一流高校的人文专业,一个人的国际背景在录取的时候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你能够看见各种国际背景的同学,来自于无数的名校,我在耶鲁短短地学习了两年,以我为例,我的老师毕业于耶鲁、哈佛、普林斯顿、斯坦福、宾西法尼亚等学校,我的同学来自于剑桥大学、东京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希伯来大学,汉城国立大学、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