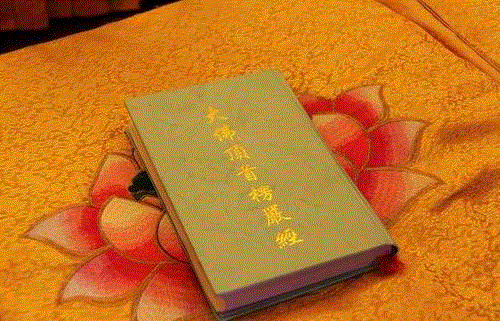试论中国佛教戒律的特点
发布时间:2022-04-10 20:25:28作者:楞严经全文网
建立对人的约束与规范是宗教的普遍特征。前者就精神而言体现着宗教间的共通性,后者,包括由此订立出来的仪轨,却是把不同宗教区分开来的主要标识。在中国哲学的范畴内,前者是体,后者是用,前者是要通过后者表现出来的。我们在论及各个宗教特点时,其实大部分是在讨论它们的不同规范。
佛教的规范称之为戒律,后来发展起来的仪轨其实也是戒律的派生。甚至说“佛教建立在戒律上,戒律是佛教的基础,其他定慧等学,都是它的上层建筑”[1],即如唐代道宣所谓“一方行化,立法须通;处众断量,必凭律教”[2]。然而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宗教,佛教在发展与传播的过程中,对应着不同的社会状况,有了戒律间的差异。
印度佛教典籍中所包含的戒律分小乘与大乘两大系统,小乘诸律后来集中在《律藏》里,大乘的戒规则散见于诸经中。此后密教又发展出一些独特的仪轨。小乘佛教有二、三十个部派,它们之间的分歧很大程度上在于戒律上有关条文和理解的差异。“例如上座部和大众部的分立主要是由于两派部众对戒行‘十事’特别是‘金银净’(僧人能否接受金银钱币)不同的认识”[3]。这些部派“由戒律不同而立异说,由学说不同而进一步变更戒律”[4]。其中有的被译成中文,有的则没有[5],有的影响很大蔚然成宗,有的则黯然冷落,甚至有的在古代中国闻所未闻。这除了机遇,对中国社会文化的适应度也是一个侧面。
佛教传入中土后,又结合华夏社会的特点发展出若干新的行为规范,如斋戒食素等。尤其是禅宗又产生了别具一格的戒规,称“禅门清规”或“百丈清规”等。但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中国的佛教徒主要遵奉的是小乘诸律,虽然中土流行的是大乘佛教,禅宗也是属于大乘的宗派。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中土所奉的小乘诸律已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其由于长期被大乘佛教徒所奉行,融合进了不少大乘的思想观念,从而在中华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具有了新的特质。
这些以汉文表述出来的佛教戒律具有以下七大特点:
第一,戒律不仅仅是规则,而且也是原则,体现着对欲望的彻底禁止[6]。“毗尼防闲三业,三业皆净,六尘自祛。圣贤践修,何莫由斯道也”[7],因为“若不以戒自禁,驰心於六境,而欲望免於三恶道者,其犹如无舟而求渡巨海乎。亦如鱼出于深渊,鸿毛入于盛火,希不死燋者,未之有也”[8]。所以说:“在三藏经典的思想中,死亡与欲望的关系是很清楚的”[9]。故其要求是“内揵既尔,外又毁容粗服,进退中规,非法不视,非时不湌,形如朽柱,心若湿灰,斯戒之谓也”[10]。于是佛教的“三法印”、“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说组成了佛教认为一切皆苦,色即如空等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生的基本态度。在这样哲学观念上构筑起来的戒律“在於防心、摄身、正口。心去贪、忿、痴,身除杀、淫、盗,口断妄、杂、诸非正言”[11]。当然体现着对各种欲望的绝对禁止,“若不以戒自禁,驰心於六境,而欲望免於三恶道者,其犹如无舟而求渡巨海乎”[12]。隋代的费长房概括道:“烦恼则五盖十缠九十八使,所行则四圣谛十二因缘,检摄七支防守三业,所受禁制则三归十戒二百五十及五百戒”[13]。这里通常所谓比丘戒二百五十条,比丘尼戒五百条只是中国佛教的一种选择,在印度“比丘戒不止二百五十,阿夷戒不止五百也”。那里“每寺立持律,月月相率说戒。说戒之日,终夜达晓,讽乎切教,以相维摄。犯律必弹,如鹰隼之逐鸟雀也”[14]。如此对行为禁止条规的孜孜追求,务必多多益善,正是把此作为解脱欲望净化自己之路。
这些看上去简直有些繁琐的禁条首先当然是因为人作为一个生命体,从维持生存与繁殖本能所派生出来的欲望无所不在,而要从中解脱出来,那就必须要到处围追堵截,防止欲望冒头滋生干扰解脱,“离五欲过故,随顺修行尸波罗蜜”[15]。鸠摩罗什所译《十诵比丘波罗提木叉戒本》将欲望比作心猿意马,将戒律比作辔勒,“心马驰恶道,放逸难禁止。佛说切戒行,亦如利辔勒。佛口说教诫,善者能信受,是人马调顺,能破烦恼军”。“夫戒者,习成性善为体”[16],规范了行为,也就纯净了心灵,“断除贪与瞋,正道灭痴愚;尘欲连根拔,宁静证圆寂”[17],克服我相带来的种种烦恼。所以诸律都是十分细密周到,简直是将生活包揽无余。佛教徒们以此为依据“费力地逐次把握每一种细微的感觉,这样,由这些相续不断的细微的感觉激发起来的许多欲望也许受到了一种自发的控制。在达到这一步之后,那些由记忆、想象和沉思所激发的欲望一定也同样被征服了”。巴姆认为:“禅那即有这样一步步接近直至完全灭欲的梯级”[18]。这也是“禅律”二者总是相连一起的道理所在[19]。
从深一步讲这种戒律实质上也是对意志产生的防止,由于“恶也同善一样,都是导源于意志的,而意志在它的概念中既是善的又是恶的”[20]。任何关于善恶的追求都是导源于意志的萌动,且势必更加远离无差别境界,所以需要处处限制自由,束缚意志[21]。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极端的苦行是一种自我虐待,也体现着一种强烈的意志,所以佛教并不提倡。甚至佛陀还反对提婆达多的极端苦行主义[22]。因此佛教戒律虽无网开一面的地方,在方法上却实行中道,也使小乘戒律在深层之目的上与大乘统一起来,彼此适用。
由上可见,虽然几乎所有宗教都把自我约束和道德追求作为实现信仰的途径之一,但佛教在理解上和方法上是其中最为突出者。佛教以在讲究中道的姿态下禁灭欲望,则和后来儒家提倡的“灭人欲”颇有相近之处。不过也会由此“以戒律太严肃,条文又繁琐,使人望之生畏,感到不易坚持,或坚持亦难到底,无形中便松弛了”[23]。实践中持戒不严的现象在古今中国佛教里成了比比皆是的现象,这确实是个重要原因。
第二,上述诸律,皆琐碎而面面俱到。这既是与上面第一条之目的相一致,也跟印度佛教教团的早期形态相合。因为“法律的主要功能不是命令而是限制,它是一种逻辑的和实际的前提”[24],戒律也一样。从佛陀时代到部派佛教时期,即使到大乘佛教流行之时,大部分的印度佛教教团都处于一种修行与生活共同体的状态。在这样的团体里,要“相与和居,治心修净”,就要“遵律度”[25],而“戒的基本意思是‘行为举止’”[26],于是“戒经以它原有的目的和意图对比丘在定居地所形成的集体生活起了组织作用”[27]。唐代的道宣生动地描绘了戒律对教团的协调组织作用:“十诵中,时僧坊中无人知时限,唱时至及打犍稚,又无人洒扫涂治讲堂食处,无人相续铺床及教人净果菜食中虫,饮食时无人行水,众乱语时无人弹指等,佛令立维那。声论翻为次第也,谓知事之次第,相传云悦众也”[28]。于是约束更多在性质上是一种修行生活中包罗万象的行为公约,因此也就必须要规定得很细很周到,才能使这个约定成为团体生活的基础。如几乎在每一条的戒相中还有开、遮、持、犯的区别,其间还要分别轻重,目的在于处置适宜。所以在有这样基础的团体中,每一个僧侣不仅处于实质公正之下,还处在程序公正之下。由于有了这样的基础,在印度“佛陀的僧团是一切教团之中最成功的,而且无疑地在组织及其它各方面胜过了其它教团”[29]。而受戒之僧众也有“和合僧”之称,“和合僧集会未受大戒者出”[30],表示正因为受了大戒,才能和合之意。中国的佛教教团同样是社会中最重要的非官方团体,并且成为滋生各类民间社团的一个基地,戒律依然是其间不可或缺的行为准则。与此同时,僧团虽是一个团体,但成佛的道路却要每个僧侣自己来走,因此确切界定每一个体在僧团中的修行与生活的空间,也是出于追求信仰的需要。
第三,体现着平等精神。无论是那一部律,它所有的条文都适应于每一位出家人,不管这位比丘或比丘尼在教团中或在社会上有何等地位,都须受同等的约束。“戒律中除了简单的长幼之分或者师生关系以外,没有包含服从的誓言,也不承认有等级。……在僧团中没有一个僧人能够向另一个僧人发布命令”[31],虽然我们在后来中国的僧团中所看到的实际情况不全如此,家长制式威权在僧官制度的催化下渐渐异化了僧团。对于世间最容易引起矛盾的财产问题,“在僧团中,佛陀依‘利和同均’原则,建立了限制私有财产,僧物公平分配的种种规则”[32]。不仅如此,列为佛戒之首的“不杀生”条,将对生命的平等尊重扩展到生物界中的一切有情物。这是世俗及其他宗教约束中所没有的,中国的僧众将此进一步具体到素食,更是将此平等观落实到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中。佛教在行为规范上的这种平等,是与其在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为无差别的涅槃相关。宗教团体中,信仰是制度的基础,故“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由此“人无贵贱,法无好丑,荡然平等,菩提义也”[33]。同时,鉴于欲望与才能的结合是推向人与人不平等的原动力,众多的戒条遮断了它们间的联系,也就铲除了不平等形成的一个根由。大乘戒律更是如此,《梵网经菩萨戒本》卷下云:“若佛子,应如法次第坐,先受戒者在前坐,后受戒者在后坐。不问老少、比丘、比丘尼、贵人、国王、王子、乃至黄门、奴婢,皆应先受戒者在前坐,后受戒者次第而坐”。在中国佛教的具体实践中,确实也出现了与社会等级观念相异的平等场景。如唐时的五台山“送供设斋,不论僧俗、男女、大小、尊卑、贫富,皆须平等供养。山中风法,因斯置平等之设”[34],对照《唐律》,就可知此风形成之不易。
第四,内在自我约束和外在规范的统一,即所谓“使制与教相应,义共时而并合”[35]。作为律,当然是一种约定的规范,存在着外在的约束力。“佛制毗尼,纠绳内众,如国刑法,画一成规”[36]。然其在执行时则是如此:“罹咎犯律,僧中科罚,轻则众命诃责,次又众不与语,重乃众不共住。不共住者,斥摈不齿,出一住处,措身无所,羁旅艰辛,或返初服”[37]。这表明对犯律者的外在约束却主要是为其自我约束创造条件,“自净其意志,是名诸佛教”[38]。正如熊十力先生指出,佛教的“戒律之本,要在不违自性戒而已”,“故戒者,自性良知之自由也”。这种体现“自当悉向天地万物一体处周流无碍”[39]的自由,符合着这样的法则:“道德法则作为有效的法则,仅仅在于它们能够合乎理性地建立在先验的原则之上,并被理解为必然的”[40]。所有的戒条虽然看起来名目繁多,僧侣为比丘者,当受二百五十戒;为比丘尼者要受三四八戒或五百戒,但都由自我来执行,并通过自我意志的坚定来贯彻到底,故其主要在道德的自我约束范畴之内。进一步讲,僧团中戒约的实施与督察,是通过羯磨形成一种以自我及他人行为评估舆论中进行的:“凡夏罢岁终之时,此日应名随意,即是随他於三事之中任意举发,说罪除愆之义”,于是“言说罪者,意欲陈罪,说己先愆,改往修来,至诚恳责”[41]。并且“谏舍此事故,乃至三谏,舍者善”[42]。这在二千多年之前确实体现了关于洞察人性的高度智慧,因为“社会的人则终日惶惶,只知道生活在他人的意见之中,也可以说,他们对自己生存的意义的看法都是从别人的判断中得来的”[43]。以戒律为标准的评论,成了走正道的最好导向。这种类似“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其内容之一,正反映了自我与外在约束的结合,从而达到印顺法师所谓的“德治与法治相统一”[44],或如陈寅恪先生所谓“佛教戒律可谓为贵族的民主宪法”[45]。说其是贵族的,在华夏传统古文献话语里就是君子的,君子之礼也与戒律一样包含着双重约束的性质[46]。
第五,戒律不仅仅是作为制恶的约束,而且是作为行善的督约。这是上一个特点的延续与扩展,故鸠摩罗什所译《大智度论》卷十三《初品中尸罗波罗蜜》云:“尸罗,好行善道,不自放逸,是名尸罗;或受戒行善,或不受戒行善,皆名尸罗”。又“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47]也被称为“通戒偈”,于此唐代湛然解释道:“过现诸佛皆用此偈以为略戒,遍摄诸戒,故名为通”[48]。即将制恶行善作为通贯戒律的基本点,其中当行善而不行善则也被视作犯戒。所以佛教戒律在道德约束上有很大的积极主动意义。这在小乘律中初露端倪,而在大乘戒法中则大为发扬了。由此所体现出来的道德全面性,所以也有人说:“在佛教中,宗教和道德律是一致的事”[49]。
第六,“释迦之教,以善权救物”,故“应世轨物,盖亦随时”[50],所以它有着具体问题具体处理的机动性,“僧团的戒律完全是根据事例而产生的”[51]。这在佛教戒律创设之始就形成了,所谓“昔甘露初开,经法是先,因是结戒,律教方盛”[52]。说得更具体一些就是“如来往昔,善应物机;或随人随根,随时随国;或此处应开,余方则制;或此人应制,余者则开”[53]。如佛陀先是听从比丘在雨中洗澡,后来有人反映比丘雨中洗澡裸形不雅,于是“从今听诸比丘受雨浴衣诸比丘尼受水浴衣”[54],让戒律切合实际情况。又据说佛陀曾遗命阿难传达:“吾般涅洹后,若欲除小小戒,听除”[55],为戒律的修订打开了方便之门。佛陀甚至允许:“从今听为破外道故,诵读外道书”[56],若“王舍城诸外道,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集一处呗诵,多得利养,眷属增长,瓶沙王信佛法僧,往诣佛所……佛言听诸比丘,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集一处呗诵说法”[57]。由此打开了佛教与其他意识交流的大门,“这一许可精神却规定了佛教的命运”[58]。更重要的是在某些方面还有“舍戒”的规定,即主要是对在家信徒而言,如有原因,有些轻戒是可以暂时不遵守的。“若受斋已,欲舍斋者,不必要从五众而舍斋也,若欲饮食,趣语一人,斋即舍”[59]。正是如此因地制宜,随机应变,才有使佛教适应中国社会的中国律学之诞生。同时,也使佛教更容易和其它的宗教,其它的意识形态和平共处,历史上佛教徒是所谓“三教合一”说最积极的提倡者[60]。
第七,戒律的实施与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相关联,所谓“追既往之罪,窥将来之福”[61],于是后者成为推行前者的动力。如《太平广记》卷三八五所引《北梦琐言》有关“僧彦先”的故事:
“青城宝园山僧彦先有隐匿,离山往蜀州,宿於中路天王院。暴卒,被人追摄,诣一官曹,未领见王,先见判官。诘其所犯,彦先抵讳之。判官乃取一猪脚与彦先。彦先推辞不及,僶俛受之,乃是一镜。照之,见自身在镜中,从前愆过猥亵,一切历然。彦先惭惧,莫知所措。判官安存,戒而遣之。洎再生,遍与人说,然不言所犯隐秽之事”。
所谓隐秽之事,肯定犯戒无疑。这故事当是报应轮回说在僧彦先昏死时从潜意识中浮现出来构筑而成,他由此“遍与人说”,当然不会再犯。此等诚如宋代范浩所言:“浮屠氏传西竺,一乘流入中国,倡天堂地狱,祸福报应之说,风动世俗,波从信向者,往往悔恶徙业而归之善,其亦有补於教化矣”[62]。这不仅是对着广大群众的,也是对着僧侣的,因为在民间传说的地狱中“僧居十六七”[63]。僧界还流传这样的歌:“酒肉中朝没阙时,高堂大舍养肥尸;行婆满院多为妇,童子成行半是儿;面折掇斋穷措大,笑迎搽粉阿尼师。一朝苦也无常至,剑树刀山不放伊”[64],来警戒那些犯戒的僧人。陈寅恪先生指出:“盖中国小说虽号称富于长篇钜制,然一察其内容结构,往往为数种感应冥报传记杂糅而成”。而唐宋以降小说在社会中流通愈广,与其内容“义主忏悔,最易动人故也”和“意在显扬感应,劝奖流通”有极大关系[65]。小说是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文学作品,佛教因果报应等道德约束观念以小说为载体,无疑对两者广泛流传,深入民间都十分有利。
上述戒律的特点基本上是小乘戒律的特点[66],不过由于我们归纳这些特点的依据是汉文的律部典籍,鉴于“佛典的汉译本身就显着受到儒教思想的规定”[67],更不用说汉人理解律的注疏了,所以其中已经搀和了大乘的约束观念,甚至是儒家的东西。不过这主体还是小乘律部的,是在早期戒律基础上阐发改造的。当然上述所谓的特点也是指其主要倾向而言,并不是绝对的。如比较比丘戒与比丘尼戒的条文,就可以看出男女之间的明显不平等。但正如不能用其平等的总体性来抹杀不平等的局部,以后者也不能据此否定前者。应该指出的是,鉴于中国的佛教徒身份的正式确定,即成为所谓七众(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是要凭据对小乘戒的接受,大乘的菩萨戒和禅宗的禅门清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作为部分佛教徒的一种附加约束,所以上述小乘律部的诸特点事实上也中国佛教戒律的主要特点。
当然上述特点还主要是文本的而非是实践的,在文本和实际之间在不同时期有着或多或少的差距,更不是一个中国佛教徒所实际感受到的规范与约束(如还要受世俗的法律与道德的管束)。但我们不能以此否定它在文本意义上的价值,因为这些以中文写着的白纸黑字规定出来的东西不仅成为塑造中国高僧的模型,重要的是,上述流传在中土的佛教戒律正是佛教中国化的基础。换句话说,佛教作为二十世纪之前唯一在中国站住脚跟的成系统的外来文化,就是得益于这些能被中国人接受的行为规范。在这个过程中佛教戒律在中国社会里进行了自身的扬弃,一些不适应中国社会文化的条文被淡化和搁置,同时一些适合中国社会的条文被推重光大,甚至发挥出新意来,并随着社会的变演而有所发展。由于宗教信徒的行为准则及其实践决定着该宗教在社会中的形态,所以戒律在中国的推陈出新造就了有别于印度的中国佛教。另一方面,以上述特点为代表的佛教戒律对中国社会的道德与法律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它的平和性,同样在中国“佛教史上只有忍辱与牺牲的记载,不曾找到战争或血腥的事实”[68]。更重要的是佛教戒律及其精神大大地深化了中华传统的道德约束机制,甚至在实践上和文本上都影响了中国的司法[69]。也就是说,佛教戒律及其约束精神也由此规范着全体中国人的行为与观念。
鉴于中国传统文化主体是由儒、道、释三家共同合成,其主要基础是在价值取向上能得到相当的一致。而这种一致又主要表现在行为规范的交叉融合上,也包括佛教戒律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鉴于这种影响在某些方面上还延续至今,因此我们在今天也就有必要对它的特点予以总结归纳,使之有更清楚的认识。
--------------------------------------------------------------------------------
[1] 参话《律宗讲要》,载《律宗概述及其成立与发展》,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版第14页。
[2] 见《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二《僧纲大纲篇第七》。
[3] 黄心川《略述南山律宗唯识观》,载《东方佛教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7页。
[4] 《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前言”,王邦维校注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5页。
[5] 据《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载,至隋代译成汉文的已有“大乘律五十二部,九十一卷。小乘律八十部,四百七十二卷(七十七部,四百九十卷,律。二部,二十三卷,讲疏)。杂律二十七部,四十六卷”。
[6] 关于对欲望的禁止,佛教中有不同的理解,但在大乘,尤其是在中国流行的大乘哲学,倾向性的意见是将贪欲和欲望有所区分。巴姆对此作了很好的阐释:“乔达摩没有说灭绝欲望,但他说灭除贪欲。贪欲就是过度的欲求。过度的欲求,无论在性质上或程度上,就是欲求将来达不到的东西。所欲与将得之间悬殊越大(指强度、持久性、量诸方面,无论那一方面),其遭受的挫折、不幸和痛苦也就越大。然而,对欲求者来说,要在实践中察觉他的欲求什么时候趋向过度,这是很困难的。那么,他该做什么?有何办法可依?也许除了‘怀疑则止’之外,不可能有经验得来的办法”。见其《比较哲学与比较宗教》,第205页。贪欲概念的难把握,也是禁止一切欲望说的一个依据。
[7] 《宋高僧传》卷十六《明律传论》。毗尼,即毗奈耶或毗那耶,律藏之音译。
[8] 竺昙无兰《大比丘二百六十戒三部合异序》,载《出三藏记集》卷十一。
[9] 查尔斯·埃利奥特《印度教与佛教史纲》第一卷第三篇,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43页。
[10] 《出三藏记集》卷十一《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第十》。
[11] 《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
[12] 竺昙无兰《大比丘二百六十戒三部合异序》,载《出三藏记集》卷十一。
[13] 《历代三宝记》卷十四《小乘录序》。
[14] 道安《比丘大戒序》,载《出三藏记集》卷十一。
[15] 真谛译《大乘起信论》,高振农校释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46页。
[16] 印顺《松山寺同戒录序》,载《华雨集》五册,南普陀寺2002年印行,第225页。
[17] 《僧伽长老尼所说偈》,载《长老偈·长老尼偈》,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3页。
[18] 均见阿尔奇·j·巴姆《比较哲学与比较宗教》,中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页。
[19] 参见拙着《江南佛教史》第六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112页。
[20]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二篇第三章,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45页。
[21] 当然对意志的束缚也是意志的一种体现。就象黑格尔所说:“意志这个要素所含有的是:我能摆脱一切东西,放弃一切目的,从一切东西中抽象出来”。同上书第15页。为了解决这个悖论,后来就有平常心即道,任其自然即禅等说法。
[22] 参见印顺《论提婆达多之“破僧”》,载《华雨集》第三册。
[23] 竺摩《“戒律学纲要”序》,载圣严《戒律学纲要》,金陵刻经处1991年版。
[24] a. passerin d’entreves, natural law: an introduction philosophy, london new york: hutchinson’s university library, 1951, p. 78。
[25] 《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
[26] a. l. 巴沙姆《印度文化史》第八章,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0页。
[27] 佐佐木教悟等《印度佛教史概说》第四章,中译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页。
[28] 《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一。
[29] 《印度教与佛教史纲》第一卷第二篇,第201、202页。
[30] дx,载《俄藏敦煌文献》第1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
[31] 《印度教与佛教史纲》第一卷第三篇,第351、352页。
[32] 昭慧《佛教规范伦理学》第七章,台北法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页。
[33] 朱棣集注本《金刚经》引“谢灵运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40页。
[34]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9页。
[35] 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二《僧纲大纲篇第七》。
[36] 《大宋僧史略》卷上“译律”条。
[37] 《大唐西域记》卷二“印度佛教”条。
[38] 见鸠摩罗什所译《十诵比丘波罗提木叉戒本》“伽叶佛说戒经”条。
[39] 熊十力《存斋随笔》,载《体用论》,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693、696、697、705页。
[40]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总导言》,载《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5页。
[41] 《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二,王邦维校注本,第113、115页。
[42] дx06581,载《俄藏敦煌文献辑录》第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40页。
[43]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二部分,第148页。
[44] 印顺《波罗提木叉经集成的研究》,载《律宗思想论集》,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第293页。
[45] 《陈寅恪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341页。
[46] 参见拙文《佛教戒律与儒家礼制》,载《学术月刊》2002年九月号。
[47] 瞿昙僧伽提婆译《增一阿含经》卷一。
[48] 湛然《法华玄义释签》卷四。
[49] 《印度教与佛教史纲》第一卷第一篇,第66页。
[50] 分见《宗居士炳答何承天书难白黑论》及孙绰《喻道论》,均载《弘明集》卷三。
[51] 《印度教与佛教史纲》第一卷第三篇,第259页。
[52] 《出三藏记集》卷三《新集律来汉地四部记录第七》。
[53] 《高僧传》卷十一《明律传论》。
[54] 参见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译《弥沙塞部和酼五分律》卷五。
[55] 《弥沙塞部和酼五分律》卷三十。
[56] 弗若多罗译《十诵律》卷三十七《明杂法之三》。
[57] 僧伽跋摩译《萨婆多部毗尼摩得勒伽》卷六。
[58] 《印度教与佛教史纲》第一卷第三篇,第283页。
[59] 失译《萨婆多毗尼毗婆沙》卷一。
[60] 请参见拙文《论“三教”到“三教合一”》,载《历史教学》2002年第十一期。
[61] 《新唐书》卷一0七《傅奕传》。
[62] 范浩《诸天阁记》,载陈树德修《嘉庆安亭志》卷十四。
[63] 《东坡志林》卷二“李氏子再生说冥间事”条,中华书局1981年版。

[64] 何光远《鉴诫录》卷十“攻杂咏”条。
[65] 见《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66] 王邦维先生认为“大小乘的问题不能与部派问题相提并论,原因之一就是大乘没有像最主要的几个部派一样,单独发展出自己完整的一套律的系统”,所谓大乘律“都不过是把大乘‘利益众生’的理论推而广之,应用到原来部派的戒律的某些条文上作一些修改、补充或扩大而已”。见其《南海寄归内法传》“前言”,第84页。但诸部律既然产生在大乘之前,称之为小乘律也未尚不可。当规范文字经过补充修改,并赋予一种新的意义时,应该是另外一种约束了。为与原来的规范区别起见,将新的规约称为大乘律,至少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方便。
[67] 中村元《儒教思想对佛典汉译带来的影响》,载《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二期。
[68] 圣严《戒律学纲要》第一章,第53页。
[69] 请分别参见拙文《论佛教道德观念对中国社会的作用》,载《上海大学学报》1994年第三期;《论佛教戒律对唐代司法的影响》,载《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