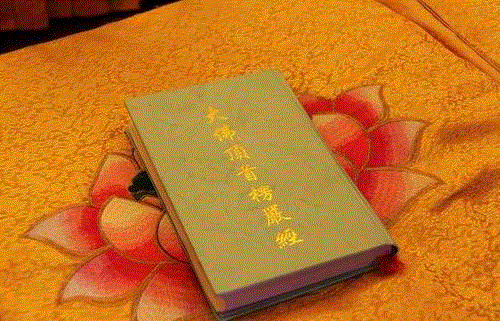近现代中国佛教的思想深度
发布时间:2022-05-19 10:03:33作者:楞严经全文网
时至近现代,以杨仁山居士创办金陵刻经处印经、讲学、弘法为机枢,中国佛教一改明清以来衰敝不振的状况,全面复兴。其波推浪涌、波澜壮阔之势,运承隋唐中国佛教之盛,而有别于隋唐佛教的则是,近现代中国佛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深度,在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乃至社会政治领域中,大放异彩,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
一、近现代中国佛教的思想使命
佛教作为一种信仰,本是以生死解脱为其终极关怀的。传统佛教也确实多以各种修行实践趋归解脱为其法要的,即便不唯侧重于个人解脱而以自利利他、利济众生为本怀的大乘佛法,也还是以共登佛地到达彼岸为终极目的。所以,佛法又被称之为出世法,是要出离世间的。
从一般意义上讲,与其他宗教信仰一样,佛教也是基于对超验世界的一种超越性体证。这种体证超越了我们的经验世界,对于经验世界中的人,对于习惯于经验世界认知方式的人,是不可思议的。也就是说,经验世界的思想方法是无法触及那种超越境界的;或者说,信仰世界是不采取经验世界的“思想”这种方法的。
但是,中国佛教在晚清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却是一个“千年未有之变局”。鸦片战争前后,随着西方船坚炮利而来的是西方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次挑战,在这一挑战面前,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都充满了危机。而在中国传统中,整个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与个人的生活态度、人生体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模式。近代中国的传统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从根本上面临着生存危机,而以此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为人生依托的个人,也必然会因此感到人生危机。这种人生危机在中国人的生命中也会被体验为一种生死抉择,需要一种有关生死的智慧来施救。这样,作为生死解脱智慧的佛教信仰就获得了一种特殊使命,它要通过应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价值体系危机来解决当时中国人生命体验中的人生危机、生死抉择。而要应对社会文化价值体系危机,佛教就要由信仰下贯为一种思想探索,以契应社会文化的“思想”特性之机。
佛教就其本身特质而言,其在中国文化中也有一种特殊的地位。一方面,佛教创始于古印度,对于中国文化而言,它是一种异质文化;另一方面,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时至晚清,经过一千多年的与中国文化的交融,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佛教已经中国化了。这样,在晚清整个中国文化都面临冲击的处境中,佛教却独具一种特殊的机缘。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中国文化处于危机之中,但危机之中又蕴含着回应挑战的需要,而作为中国文化主流价值形态的儒道,已经直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岌岌可危。这时,虽然已是中国文化组成部分之一,但始终还保持了其一定的异质性的佛教,正适应了中国文化回应西方文化挑战的需要,成了中国文化可以回应西方文化挑战的可资凭借的一块主阵地。
当然,近代中国社会因为社会文化价值体系危机而产生的人生危机,毕竟与一般生死问题还是有所区别的。与生死问题相比,这种人生危机含有了更多的社会文化思想内涵。那么,要解决这种人生危机,除了要有生死智慧这种终极依据外,还需要更多的思想性方法,而这对传统佛教来说则是一种新的要求,需要传统佛教也进行自己的思想探索。当然,佛教是以其信仰为其特质的,怎样将这种信仰下贯调适为适当的思想,就成了近代中国佛教必须解决的时代课题。这是近代中国佛教的思想使命,近代中国佛教界、思想界精英承应这一使命,进行了大量深入的探索。
二、作为思想伏流的近代中国佛教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晚清思想家有一伏流,曰佛学。前清佛教衰微,高僧已不多,即有亦与思想界无关系。……石埭杨文会,少曾佐曾国藩幕府,复随曾纪泽使英,夙栖心内典,学问博而道行高。晚年息影金陵,专以刻经弘法为事。至宣统三年武汉革命之前一日圆寂。文会深通法相、华严两宗,而以净土教学者,学者渐敬信之。谭嗣同从之游一年,本其所得以着《仁学》,尤常鞭策其友梁启超。启超不能深造,顾亦好焉,其所着论往往推挹宗教。康有为本好言宗教,往往以己意进退佛说。章炳麟亦好法相宗,有着述。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梁启超将近代中国佛学论为思想界的伏流,而这一伏流的源头就在于杨仁山(文会)居士。
杨仁山居士创办金陵刻经处,印经、讲学、弘法,全面复兴中国佛教,这一宏大事业的深入推展,基于他考察对比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后达到的一种深刻的思想认识。他说:“泰西各国振兴之法,约有两端:一曰通商,二曰传教。通商以损益有无,传教以联合声气。我国推行商业者,渐有其人,而流传宗教者,独付缺如。……今欲重兴释迦真实教义,当从印度入手,然后遍及全球。庶几支那声名文物,为各国所器重,不至贬为野蛮之国矣。”(《支那佛教振兴策》)在杨仁山居士看来,西方各国富强的原因,除了通商发展经济外,另外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以宗教信仰凝聚人心。关于经商使国家富强这一点,当时中国人已基本上意识到了,并且有了洋务运动等实际举措,但是,对于以宗教信仰凝聚人心而使国家富强这一点,当时中国人还普遍没认识到这个层面。其实,在西方,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已经有马克斯·韦伯这样的思想家进行了深刻的论述。韦伯认为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着深层的关联。这种认识说明了宗教信仰下贯转化为现实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精神思想理念,对于推动现实社会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我们还不知道马克斯·韦伯等西方思想家的这类思想论述,与杨仁山居士的这种思想有没有渊源关系,但很明显的是,杨仁山居士的这种思想在中国思想界是前所未有的,具有开创导引意义。
当然,杨仁山居士印经、讲学、弘法事业,还是从佛教的方面来落实他传教以联合声气、振作国势的理念的,而其后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这些所谓新学家们,则是从社会思想这个方面来以佛教理念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进而回应时代挑战,变革社会,推进国家发展的。
康有为这位变法维新的倡导者,正是以佛教式的大同理想为动因来推进变法维新运动的。康有为的大同理想以“去苦界至极乐”为终极目标。在他看来,“诸苦之根源,皆因九界”:“一曰国界,分疆土、部落也;二曰级界,分贵贱清浊也;三曰种界,分黄白棕黑也;四曰形界,分男女也;五曰家界,私父子、夫妇、兄弟之亲也;六曰业界,私农工商之产也;七曰乱界,有不平、不通、不同、不公之法也;八曰类界,有人与鸟兽虫鱼之别也;九曰苦界,以苦生苦,传种无穷无尽,不可思议。”而“救苦之道,即在破除九界”:“第一曰去国界,合大地也;第二曰去级界,平民族也;第三曰去种界,同人类也;第四曰去形界,保独立也;第五曰去家界,为天民也;第六曰去产界,公生业也;第七曰去乱界,治太平也;第八曰去类界,爱众生也;第九曰去苦界,至极乐也。”(《大同书》)康有为用佛教的平等理念观照现实社会,认为“生兹九界,投其网罗,疾苦孔多。……何以救苦?知病即药,破除其界,解其缠缚。”(《大同书》)基于这种认识,康有为“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以经营天下为志”,发起推动变法维新运动,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
但是,这种变革在积弊深固的近代中国举步维艰,谭嗣同等仁人志士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谭嗣同曾拜杨仁山居士为师,从其研究佛教一年。谭嗣同深感社会现实的黑暗,而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又像一张罗网笼罩着这一切,难以改变,他苦苦以求“一种冲决网罗之学”,终于在佛教中找到了。他认为:“举凡独夫民贼所为一切钳制束缚之名,皆无得而加诸,而佛道以独高于群教之上。”(《仁学》)他用佛教理念镕铸一切新旧之学,着《仁学》,“别开一种冲决网罗之学”,形成了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无畏的战斗精神,他甚至以佛教发愿的意趣凝成一种“以心挽劫”的心力。他说:“以心挽劫者,不惟发愿救本国,并彼强盛之西国,与夫含生之类,一切皆度之。……以此为心,始可言仁,言恕,言诚,言挈矩,言参天地、赞化育。以感一二人而一二化;则以感天下而劫运可挽也。”(《仁学》)正是本着这种“以心挽劫”的无畏精神,谭嗣同慷慨赴死,为变法维新献出了生命。
戊戍变法失败了,现实中的变革是非常艰难的。经历了戊戍变法的失败,梁启超认识到了中国人的精神状态的改变是社会变革中的关键因素,而人的精神状态中的关键因素又在于信仰,他说:“凡一国之强弱废兴,全系乎国民之智识与能力;而智识能力之进退增减,全系乎国民之思想;思想之高下通塞,全系乎国民之所习惯与所信仰。”(《论支那宗教改革》)怎样才能以一种信仰的力量来改变国人的精神状态呢?梁启超认为应该以佛教“无我”的理念来破除“心中奴隶”,因为“今天众生之大蔽,莫甚乎有我之见存。有我之见存,则因私利而生计较,因计较而生挂碍,闻邻榻呻吟而不动心,视同胞国民之糜烂而不加怜,任同体众生之痛痒而不知觉。”(《论支那宗教改革》)在梁启超看来,以佛教无我的理念,破除心中的我痴、我执、我慢、我见,破除心中奴隶,就可以新民智、新民德、新思想、新习惯,直至新信仰,这样,才能有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而中国才有变革发展富强的希望。
民众精神状态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最重要作用的部分还是道德,一个社会的维系乃至发展,除了制度层面的保证外,在制度之上起作用的就是道德。章太炎看到了道德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并且看到佛教在这方面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他说:“至所以提倡佛学者,则自有说。民德衰颓,于今为甚,姬孔遗言,无复挽回之力,即理学亦不足以持世。……恶慧既深,道德日败,矫弊者,乃憬然于宗教之不可泯绝。”(《人无我论》)对于重塑国人道德,在章太炎看来,可以发挥作用的是佛教,复兴佛教,不仅可以改变国人衰颓的道德状况,而且可以藉此推动社会革命,他说:“所以提倡佛教,为社会道德上起见,固是最要;为我们革命军的道德上起见,亦是最要。总望诸君同发大愿,勇猛无畏。我们所最热心的事,就可以干得起来了。”(《革命道德说》)
从杨仁山居士将复兴佛教与振兴国势联系起来提倡阐扬,经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以佛教平等、唯心、无我等理念镕铸社会思想、推动社会变革,到章太炎提倡以佛教重建道德、发起革命,与西方近代经过宗教改革使基督新教伦理在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也有了思想取向上的一致,这也许透显了某种普遍的必然性。在社会文化价值体系大变革时期,社会思想层面的深刻变革,必然会牵动信仰层面的联动。信仰作为超越层面的东西,虽然具有一定的超稳定性,但对社会思想环境的巨大变化,它也必然会对这种巨大变化发生反应,并且这种社会思想的巨大变化能发生乃至完成,也还需要信仰层面的联动,因为说到底,社会思想在根本上是深深扎根于信仰之中的。当然,近代中国社会思想变革所引起的近代中国佛教的联动,更多的还是佛教作为一种信仰的下贯,而真正意义上的佛教本身信仰层面的反思调适,则是在现代中国佛教人间佛教思潮中得到了一种深刻的体现。
三、现代中国人间佛教的思想意义
可以说,太虚大师倡导的人间佛教思想,正是在近代中国佛教思想探索的基础上,回向佛教本身的一种主体性反思。
人间佛教的倡导,首先是对传统佛教中“死鬼的”、“天神的”偏向的对治。明清以来,传统佛教的内涵越来偏向于荐亡度鬼的重死重鬼的经忏佛教,这种专注于死鬼领域而大兴经忏佛事的佛教,使佛教对现实社会人生很少关注,离人们的现实生活越来越远,而人们也终于离这种佛教越来越远。但是,佛教的真精神却并非这样,太虚大师说:“佛教并不脱离世间一切因果法则及物质环境,所以不单是精神的;也不是专为念经拜忏超度鬼灵的,所以不单是死后的。在整个人类社会中,改善人生的生活行为,使合理化、道德化,不断的向上进步,这才是佛教的真相。”(《人生的佛教》)从对治死鬼的佛教这一角度,太虚大师提出了人生佛教,在此基础上,印顺法师又针对印度佛教后期重视天神的倾向,从《增一阿含经》所言“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得到启发,侧重提倡更重视人间生活的人间佛教,他说:“虚大师说‘人生佛教’,是针对重鬼重死的中国佛教。我以印度佛教的天(神)化,情势异常严重,也严重影响到中国佛教,所以我不说‘人生’而说‘人间’。希望中国佛教能脱落神化,回到现实的人间。”(《游心法海六十年》)
本来,无论是“死鬼”,还是“天神”,都是传统佛教的题中之义。作为对超验世界的体证的佛教信仰,自然会涉及死亡、鬼神、天界、地狱等超验领域,但这些超验领域毕竟不是理性思想所能思议的,而近现代西方理性主义的影响深入人心,深刻地改变了西方文明,也有力地在近现代中国产生影响。这就是近现代中国佛教的新机缘。中国佛教面对这种重视理性思想的新机缘,当然有必要因应这个新机缘进行调适,然后才能契机地弘传佛法。
怎样进行这种调适?除了明确将佛教的重心调向现实人间人生外,还要从佛教信仰的高度适当地转化出可资思议的思想基础,通过建立佛教信仰性的思想基础,进而对社会思想产生一种导向意义。
人间佛教建立的这一思想基础,就是太虚大师的“真现实论”。
太虚大师“真现实论”,从佛教信仰核心法则——缘起法则出发,揭示出了我们人间社会现实,应该是以“变”为其机枢的。
性空缘起,发生了生命的本真事情——现实,那么,这现实的本性也就是缘起变现之变,而这正是与“现前事实”之传统现实观不同的根本之处,也是太虚大师“真现实论”之真。
太虚法师《真现实论》将这种真现实分解为四重:“第一、‘现变实事’曰现实者,唯现在显现而变动变化着的,始为实有之事,故曰‘现实’。此理与平常所云之现实,已较精深,然其义尚不止于此。第二、现变实事缩称之为‘现事’,明现变实事真实理性之‘现事实性’,始曰现实。第三、缩现事实性曰‘现性’,于此现性能实证觉,谓之‘实觉’。如是现性实觉始曰现实。第四、复将前义缩为‘现觉’,即一切法现正等觉。于此现觉圆成实际上穷神尽化之变用,谓之‘现觉实变’。”现变实事——现事实性——现性实觉——现觉实变,这四重现实观,以变始,又以变终,是以变为贯穿始终的主线的,这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这种变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变呢?
应该说,四重现实观中的变虽然是贯穿始终的,但其始终之变又是有差异的,第四重现实——“现觉实变”之变,与第一重现实——“现事实变”之变,是不同的。“现在显现而变动变化着的”“现变实事”之变,主要是一种现象描述,是对作为一种现象的现实相状的自然描述,而“于此现觉圆成实际上穷神尽化之变用”的“现觉实变”之变,就是对这种真现实之变的性质的说明。当然,这种说明经历了“现事实性”、“现性实觉”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蕴藏在“现变实事”这种现实现象中的人的因素,逐渐显现出来。如果说作为“现变实事真实理性”的“现事实性”,还仅限于说明“现变实事”这种现实现象的内容,还没有显现出人的因素的话,那么,于“现事实性”上“能实证觉”之“现性实觉”,就明白无疑地显现出作为现实现象内容的“现事实性”中人的因素了。作为现实现象内容的“现事实性”,绝非客观对象化的所谓现象的本质,这种作为现实现象内容的“现事实性”,根本上其实就是属人的。唯有属人的,为人所能实证而且已经实证了的对“现事实性”的“现性实觉”才是现实的,而不属人的,不能为人所实证的一切所谓客观对象的属性,都不能说是现实的。
而“现性实觉”作为一种现实,又绝非认识论意义上的一种主观认识而已,这种“实觉”,是“感而遂通”式的,是可以而且应该产生实际“变用”的,这便是“现觉实变”。
现变实事——现事实性——现性实觉——现觉实变这四重现实观,揭示了不同于对象化存在式的“现前事实”之现实的“真现实”,其“真”就在于现实之实根本上就是唯识现、众缘生的,是始终处于变现中的,绝非实体性的存在,而是变现的“缘”在。
普通社会思想,从根本上来说,是将原本的真实的生命、生活现象分析厘定为静态的、稳定的、明确的范畴以便于把握,然后进行理性思维的思想。所以,这种思想是将人间社会现实厘定为一种静态的东西去分析思考的,这样就会对世界产生静态的、固定的看法,由此产生各种各样佛教所谓的执着,偏离世界本来的真实相状,产生偏差、错误,也最终形成佛教所说的人生的苦恼。这种苦恼的人生的根源,其实就在于普通思想方式将真实的变化着的现实社会人生“理解”成了各别不变的东西的组合,而太虚大师人间佛教“真现实论”思想,却以佛教缘起法则的智慧观照,将普通思想视野中不变的静态的现实观,还原成了真实的、变化的现实。它提供了把握变化着的真实的现实的思想方法,扩展了思想本身可能达到的领域,这是普通思想视野中所没有过的一种思想方式,可以引导人们突破普通传统思想方式的种种迷思执着,在无尽缘起的变化发展中,达成一种随缘成就一切资生事业而回向快乐的健康的人生。人间佛教真现实论的不同寻常的思想深度和思想意义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