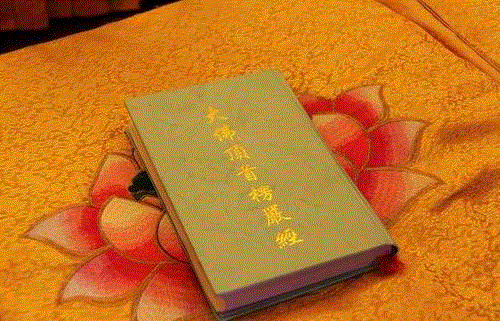金陵刻经处与近代佛教教育
发布时间:2022-09-20 11:31:49作者:楞严经全文网金陵刻经处与近代佛教教育
吕建福
传统佛教之培育僧材、续佛慧命,主要靠早期寺院的译经讲学及唐以后建立的丛林制度。丛林制度最早虽由禅宗大德所创,所谓“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但后来佛教寺院凡规模较大者,无论宗门、教下,几乎无不实行丛林制度。这是因为它改变了印度佛教的游方乞食等不适应中国文化与社会的做法,僧众可以自食其力、安居修道,而培育人才、续佛慧命之功用自在其中。千余年来,佛教的人才基本由丛林制度所培育。在今天看来,佛教丛林中实施之佛教教育,实为“知行合一”的教育,是传统的、也是合乎佛法特质的“如法”的教育,有足资近现代新式佛教教育所珍视者。然法久弊深,到了清朝末年,传统寺院丛林已积弊重重。自本世纪初所兴起的新式佛教教育,基本是学院式教育,即佛教界兴办与社会学校相仿之佛学院来培养佛教人才,乃佛教发展至近现代适应社会、契机弘化的必然。
近代佛教教育的兴起约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佛教外部的原因,主要是社会政治的原因。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以佛道寺观产业的十分之七充作社会教育之资,兴起“庙产兴学”运动,并获朝廷允准实施,由此而激发佛教界以寺产兴办僧教育兼办普通教育的热潮。动因本在保护佛教寺产,实际则成为近代佛教教育兴起的契机。二是佛教内部的原因。传统佛教丛林经过一千余年,到了清朝末年已积弊重重,丛林寺产极为丰厚,却不仅不再能培养僧材,弘续佛法,反成了障道因缘。“一般僧寺多以贩卖如来家业争取货利,以财富为荣、名利为尚。向上一着,早无人问津。”(1)当时名山大刹,数百僧众中,能写三百字书信者也不多,可见教育水平之低下。杨仁山居士因此慨叹当时“僧徒安于固陋,不学无术,为佛法入支那后第一坠坏之时。”(2)当时之寺院,许多成了社会上一些无职业者的谋生庇护处。佛教规模虽存,却徒有空壳,早已丧失了大乘佛教的精神和活力。这是佛教界必须自我改革而以丛林寺产兴办佛教学堂、培育僧材、振兴佛教的内部原因。其三是文化层面的原因,较之社会层面的原因可能更为深刻。清末中国社会正值国门初开、中西文化推排激荡之时,当时面对西方列强,有国家民族之危机;面对造就船坚炮利之西方文化,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也出现了危机,从而有中西体用之争,于今未息。佛教为中国传统文化之重要部分,值此时势,无论为佛教自身,还是为国家社会,都有反思和变革之驱力。因此,近代新式佛教教育的兴起,除了有保护寺产、维护佛教的动机外,更有振兴佛教的理想,乃至有以佛教拯救国家民族的危机和向全世界弘扬佛法的愿望。基于这一文化层面的原因而兴办的新式佛教教育,起点是较高的。金陵刻经处于本世纪初兴办的佛教教育,即是这样一种高起点的新式佛教教育。
在金陵刻经处创办“祗洹精舍”之前,已有江苏扬州天宁寺于1906年开办的“普通僧学堂”,由释文希主持。就时间而言,这是近代史上由国人开办的第一家新式僧学堂。在此之前,日僧水野梅晓曾于长沙开办僧学堂,1899年南京“日本净土真宗本愿寺”也曾开设“东文学堂”,但皆非国人所办。释文希于扬州天宁寺所办的僧学堂,资金来源于镇江、扬州各大寺院。各大寺院出资动因只是藉办学作为保护寺产的手段,并无兴办僧教育以培育人才的理想,因此不久即与释文希发生冲突。最后释文希被捕,扬州僧学堂因此停办。杨仁山居士曾对扬州僧学堂寄予厚望,并希望镇江之金山寺、常州之天宁寺也开办僧学堂,但他对“各寺住持僧安于守旧”有深刻的认识,深知“非得大权力以鼓动其机,不能奋发有为也。”(3)
扬州僧学堂停办的第二年,即1908年,杨仁山居士于金陵刻经处创办“祗洹精舍”。杨仁山以居士身而兴办僧教育、培育佛教人才,不无对传统佛教界办新式僧教育的失望,更主要是出于他对当时佛教衰弊的洞察。杨仁山认为佛教式微的关键在于缺乏人才。“盖自试经之例停,传戒之禁弛,以致释氏之徒无论贤愚,概得度牒;于经律论毫无所知,居然作方丈,开期传戒。”(4)由于试经、传戒等古制的弛废,而造成出家众素质低落,“安于固陋,不学无术”。因此,振兴佛教之机,首先在于人才的培养。事实上远在扬州普通僧学堂之前许多年,杨仁山就已有兴办僧教育的创议:
“欲求振兴,惟有开设释氏学堂,始有转机;乃创议数年,无应之者”(5)。
杨仁山于1878年曾随曾纪泽出使英法,前后有三年之久,考察了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宗教等制度,具有同时代一般人——尤其是当时佛教人士所难得的开阔视野和洞察力。他深刻认识到“斯世竞争,无非学问”,而佛教的兴衰也全系乎此。落到实处,即在提高出家众的素质,培养优秀僧材。因此,杨仁山居士倡导新式僧教育就时间而言可以说是近代佛教史上最早的人物之一,而在办学思想上更有同时代一般佛教徒难以企及者。金陵刻经处以杨仁山居士所捐献私宅为基业,并赖十方信众护持,为一刻印流通佛教经典之所,并非一般僧寺,自无以办学保护寺产之考虑。祗洹精舍的办学经费,基本由各界捐助,办学理想极其宏大。祗洹精舍创办时间虽在1908年,其缘起可上溯至1893年。当时杨仁山居士与锡兰摩诃菩提会达磨波罗相识,达磨波罗欲振兴世界佛教,而拟从复兴印度佛教开始。祗洹精舍创办一大动因,即在培育人才赴印度弘法,由印度而遍及世界。由此可见祗洹精舍办学目标之远大,非后来一般之佛学院可比。这也是杨仁山居士弘法之愿心和开阔之视野的体现。早在1878年他42岁时,即有弘扬世界佛学的想法。在与南条文雄通信中他写到:“弟潜心净域十余年,愿持迦文遗教,阐扬于泰西诸国。”(6)后来他在《支那佛教振兴策》中又写到:“统地球大势论之,能通行而无悖者,莫如佛教……今欲重兴释迦真实教义,当从印度入手,然后遍及全球”。(7)
杨仁山以金陵刻经处为基础创办祗洹精舍,深察当时佛教之衰弊,迥异于一般“动机多在保护寺产”之普通僧学堂,纯为培育弘法人才、振兴佛教而兴学,且有弘扬世界佛学的宏大视野,对于近代佛教教育而言,实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诚如印顺法师在《太虚大师年谱》中所说:“为佛教人才而兴学,且有世界眼光者,以杨氏为第一人。”(“宣统一年按语”)
祗洹精舍的规模虽然不大(当时招收学生约20余名),但其教育思想和教育体制在当时是相当先进的。杨仁山曾通过南条文雄了解日本“佛教各宗大小学校种种章程”(8)来规划祗洹精舍的教学内容和制度。杨仁山所构思的僧学堂,参照社会学校的体制,“仿照小学、中学、大学之例”,各为三年,乃九年制学校。前三年学习基础经论,如《四十二章经》、《佛遗教经》、《八大人觉经》、《唯识三十论》等,学成为“初等”,可准受沙弥戒;后三年学稍深之经律论,学成可受比丘戒,为“中等”,并给度牒;最后三年研修教、律、禅、净等专门之学,学成能讲经说法者,为“高等”,可准受菩萨戒,并换牒。杨仁山认为,九年学成,“方能作方丈,开堂说法,升座讲经,登坛传戒,始得称大和尚”。仅受初等、中等僧教育者,只能任寺院一般职事。而未受僧教育者,不准出家。不能学者,仍命还俗。(《释氏学堂内班课程刍议》)
由此可见,杨仁山居士所构想之僧学堂,已不仅仅是一般的佛教教育、培养人才而已,而是将佛教的教育制度与僧伽制度结合在一起,出家、受戒、任职等资格与教育制度有相应的关系。未经三年初等教育,学习普通知识及基础经论,不得受沙弥戒。若三年初等教育也不能合格完成者,则令其还俗。这样佛教教育制度就为僧尼的基本素质提供了保证。而必通达教理、专精一宗或数宗之高等教育后,方能作方丈、升座讲经,更成为佛教高级人才之纯正无讹的保障,可以杜绝以盲引盲、“滥附禅宗、妄谈般若”等大弊。杨仁山居士深察当时佛教界习弊而有此构想。这一将佛教教育制度与僧制结合起来的构想,在当时实是一种创见,也是对传统僧制的大胆改革,杨仁山认为如此方能提高全国僧尼素质。这对后来的佛教教育颇有影响,在今天仍不失其价值,值得重视。太虚法师后来倡导“教制革命”、整理僧伽制度,从杨仁山居士的构想中已见端倪,也是杨仁山居士佛教革新事业的继续。
此外,杨仁山认为释氏学堂还应设“普通学”,包括语文、算法、史学、地理、梵文、英文、日文等。在这方面,他借鉴了基督教传教办学的方式,认为佛教学堂可分教内、教外两班,外班以普通学为主,这实际上就是由佛教界来办社会教育。这既合乎大乘佛教教义,也易为当时“庙产兴学”风潮下许多人所接受。内班则以佛学为主,但也兼习普通学科。杨仁山所开列的普通学中,外语占较大比重,这是因为他一直有将佛法弘扬至西方的心愿。在这样的释氏学堂中修学佛学并兼学普通学的出家人,将是兼通内外学的现代僧人。后来各地之佛学院,大多也都设有普通学课程。

祗洹精舍实际开设有佛学、汉文、英文三门课程。汉文是研究汉文佛典的基本修养;英文则是通往西方的基础,也是欲赴印度弘扬佛法和学习梵文的工具语言。佛学乃根本课程,当时曾聘苏曼殊任英文教师,李晓暾为汉文教授。佛学课程,杨仁山曾请式海法师任讲席,后因故未能应聘,杨仁山遂自任讲席,讲授《大乘起信论》和《楞严经》(9),后又延请台宗名僧谛闲法师任学监并开讲天台教观。由此可知祗洹精舍之名为“居士道场”,实为居士所创办之佛教道场,其时并无明显的居士与出家僧之分别与争论,与后来内学院一系有所不同。杨仁山居士佛学修养精纯,弘法之胸怀也博大,当时名僧月霞法师尊为大愿菩萨示现,对杨老居士极为尊敬,并四处募款助成杨仁山之佛教事业。后祗洹精舍停办,月霞法师1914年至上海创办近代着名之华严大学于哈同花园。
另外值得重视的是,杨仁山倡导的佛教教育相当重视修行。在他所规划的九年制佛教教育中,不仅列有学习课程,也列有修行内容,将朝暮课诵列为前三年之例行功课。后几年由中等至高等之学习,研修“专门学”,也注重学修并重,并非纯学术之研究。他在“释氏学堂内班课程刍议”中强调:
“专门学者,不但文义精通,直须观行相应,断惑证真,始免说食数宝之诮。”
杨仁山居士后来又于金陵刻经处创办“佛学研究会”,于“小引”中也强调“由信而解,由解而行,由行而证”,遵循佛法“信、解、行、证”之次第,并不赞成纯粹的学术性研究。杨仁山居士本人于公务繁忙之际仍“诵经念佛或静坐作观”,“教宗贤首、行在弥陀”是他一生学修并重的写照。解行并重是修学佛法的原则,也是传统佛教丛林教育的一大优良传统。杨仁山所倡导的新式佛教教育,在形式上虽参照社会学校的教育制度,在内容上仍继承了传统丛林制度佛教教育知行合一的优良传统,非如后来一般佛学院虽也强调学修并重,但大多受了新式学院教育的影响,重学而轻修。今日佛教界关注之“信仰建设”、“道风建设”等,也可从佛教教育继承丛林制度解行并重的优良传统、真正注重“学修一体”着手。祗洹精舍当时招收的学生大多为镇江、扬州各大寺院的年轻僧人,也有在家居士,缁素共约20余名。人数虽不多,但后来许多成为近代佛教之弘法健将或佛学名家,可以想见祗洹精舍教学质量之高,实乃近代佛教史上第一所名符其实的高等僧学堂。其中着名者有太虚法师,后来成为近代佛教革新运动的领袖;仁山法师,乃“大闹金山寺”的主角,促进了近代佛教的变革;智光法师,后创办儒释初高小学、焦山佛学院等,从事佛教教育多年;另有栖云、观同等,都是当时的着名人物。居士中有邱?明、谢无量等,为佛学名家。欧阳竟无、梅光羲、李证刚等,虽非祗洹精舍实际招收的学生,但在祗洹精舍成立前后一直追随杨仁山学佛,助成佛教事业,可以说也是祗洹精舍中的人物。
杨仁山于金陵刻经处创办祗洹精舍,兴办佛教教育,虽为时短绌(因经费不敷等原因,祗洹精舍前后不足两年),但影响极大。作为近代佛教史上第一所高等僧学堂,它不仅为近代佛教复兴造就了一批卓越的人才,更为后来的佛教教育提供了一种榜样。祗洹精舍所培养的僧俗两众人才,薪火相承,至今仍在为佛教事业作出贡献;祗洹精舍所提供的新式佛教教育模式,对近代佛教教育具有深远的影响。欧阳竟无居士先就金陵刻经处成立“研究部”,后以研究部为基础创立近代佛教史上着名的“支那内学院”,继承和发展杨仁山的佛教教育事业,其所培养或影响的一批着名佛教学者,对近代佛教学术文化贡献极大。太虚法师后来致力于佛教改革,新式佛教教育是他整个佛教革新事业的重要基础。太虚的佛教教育事业深受祗洹精舍的影响。他入学祗洹精舍时年仅21岁,乃是因对一般僧教育组织有不少“徒拥虚名”或过于随顺潮流而“失却佛教立场”甚或“俗化成饮酒吃肉”的失望,忽闻金陵刻经处创办祗洹精舍,为其宏大格局所吸引,认为是一“世界佛教运动的组织”(10)而加入。后来他所创办的许多佛学院,也格局宏大,武昌佛学院后更名为“世界佛学苑”,在教育思想、教育制度、课程规制上,也受祗洹精舍的影响。太虚早期创办之“觉社”(1917),其中有“佛教大学院”,太虚自谓“仿照金陵杨仁山居士之祗洹精舍,加蒙藏梵文,期以五年”(11),可以说是杨仁山佛教教育事业的直接继承。
金陵刻经处世纪初的佛教教育事业,对近代佛教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太虚法师曾评价说:“祗洹精舍虽然办了不久即停顿,其影响后来的佛教事业实大”。(12)
释东初在《中国佛教近代史》中写到,祗洹精舍为时虽短,“却为中国佛教种下革新的种子,无论于佛学的发扬,或教育设施,以及世界佛化推进,无不导源于此”。(13)评价至高。因此之故,有的学者认为金陵刻经处不仅是近代佛教一重要的研究和出版机构,同时又是“近代佛学教育的中心”。(14)
另外值得重视的是,金陵刻经处于本世纪初所兴办之佛教教育,除了它所作出的实际贡献和具有的影响外,还为近代佛教教育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传统佛教教育二千年来都是依托于寺院丛林,局限于宗教界,这固然有其保存佛教优良传统等优势所在,但传统教界一定程度存在的保守倾向和某些积弊,也必然对新式佛教教育产生制约,影响近代佛教教育的发展。杨仁山以居士身而办僧教育,依托于金陵刻经处而非佛教寺院,居于宗教界和社会文化界之间,在形式上可以说是全新的。金陵刻经处为一集佛学研究、佛经出版和佛教教育于一体的佛教文化机构,在当时也是一个社会民间团体,不仅有佛教界法师的支持,许多方面也有赖社会人士的护持(如祗洹精舍的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陈三立,当时陈三立正督办南浔铁路),从其人员、经费、管理、事业各方面来说,都已迥异传统寺院,而其佛教文化事业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也不仅局限于佛教界,而是与社会文化交汇,对当时知识界和社会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有学者认为,“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金陵刻经处对近代文化的贡献,其实不仅在于佛法弘扬之本身,而且在于它将居士道场、图书出版、高等教育合而为一的建设新文化的尝试,近世佛法勃兴实有赖于此。”(15)就佛教教育这一课题而言,祗洹精舍的高等僧教育,依托于金陵刻经处这一独特的佛教文化机构,既摆脱了清末传统佛教界的种种习弊和禁锢,又有佛经出版和佛学研究为其坚实的学术文化基础,由此保证了其高等僧教育的质量。它的成功经验,值得今后佛教教育事业认真研究和借鉴。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对金陵刻经处的佛教文化模式深有体认,称其为“集研究、讲学、刻经于一体的佛教弘法利生机构”(“金陵刻经处130周年祝词”),九旬高龄仍挂怀刻经处的佛教教育事业,谆谆嘱咐“恢复仁山先生、竟无先生创导佛学研究、培养佛教人才的事业”(1995年11月),祝愿金陵刻经处的“讲学刻经事业日进日新”!今天距杨仁山居士当年倡导佛教教育几近整整一个世纪,由于种种历史因缘,佛教界人才青黄不接、僧众素质偏低的现状仍为一严峻的现实。缅怀杨老居士当年的宏愿悲心及其辉煌的佛教事业,我们相信,今天有政府热心支持佛教文化事业的政策,有赵朴老等老一辈大德法师和居士的心量识见、悉心护持,有年轻一代佛教人才的真实发心、精进不懈,以我们今天的时代和条件,并不亚于百年之前,今日佛教界(包括金陵刻经处)之佛教教育培育人才、续佛慧命的事业,是必定能再创辉煌的。
注释:
(1)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第99页。
(2)杨仁山,《等不等观杂录》卷一,“送日本得大上人之武林”。
(3)杨仁山,《等不等观杂录》卷五,“与陶森甲书”。
(4)杨仁山,《等不等观杂录》卷一,“释氏学堂内班课程刍议”。
(5)杨仁山,《等不等观杂录》卷一,“般若波罗蜜多会演说一”。
(6)杨仁山,《等不等观杂录》卷七,“与南条文雄、笠原研寿书”。
(7)杨仁山,《等不等观杂录》卷一。
(8)杨仁山,《等不等观杂录》卷八,“与南条文雄书二十七”。
(9)蒋维乔,《中国佛教史》卷四;印顺,《太虚大师年谱》“1909年”。
(10)太虚,《太虚大师全书》,“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
(11)太虚,“觉社宣言”,《海潮音》第一期。
(12)太虚,《太虚大师全书》,“优婆夷教育与佛化家庭”。
(13)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第80页。
(14)宋立道,“杨仁山的佛教理念”,载《金陵刻经处1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5)麻天祥,“金陵刻经处对近代佛教文化的贡献及对未来文化建设之启迪”,载《金陵刻经处1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