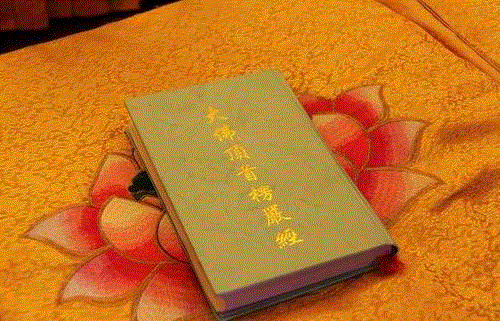大勇阿奢黎传略
发布时间:2022-07-17 12:55:26作者:楞严经全文网大勇阿奢黎传略
天晟传统文化研究所 陈士东
大勇阿奢黎俗名李锦章,1893年生于四川巴县,清末毕业于法政学校,民国初年充任军政、司法等要职,曾为《国民公报》的主笔,于军界颇有影响。不久,他与佛源法师在重庆建香光学社,此是他与佛教结缘之始,但这时只是以居士身份活动。1918年,黄葆苍至重庆,与董慕舒及大勇共结为法友,三人发心深切,誓愿出家专修以事佛法之弘扬,这是他出家之因缘。民国八年即公元1919年5月7日,这天农历是4月初八,为世尊释迦牟尼圣诞日,他与黄葆苍、董慕舒师从太虚大师,同日剃度于宁波归源庵。黄之表字为大慈,董之表字为大觉,他法名传众,表字大勇,时方27岁。同年6月,竹溪法师约太虚大师赴京处理事务,太虚以觉社事委托于大勇代管。1920年,他受具足戒于金山江天寺,并于此寺学了一段时间的禅宗。1920年秋,大勇、玄义等路过五台,因法尊等请求开示,而住静于五台山,并顶礼文殊菩萨。这次法尊与大勇法师相见,结下了深厚的法缘,听其为略讲《八大人觉经》,后又讲《佛遗教经》。1921年夏,法尊又从大勇听受《弥陀经》等。同年秋9月6日,因太虚大师于北京弘慈寺讲《法华经》,大勇自五台至北京听讲,除了听受《法华》之外,于法会期间,大师还为大勇、王虚亭等讲《金刚经》,大勇法师笔录有《金刚义脉》。自法师与佛教结缘至此段期间,可以算作是他学习显宗之经过。

关于法师与密宗之因缘,亦是兴起于太虚《法华》一会,时在北京弘密的日本东密大师觉随亦来参听,屡以唐代传日本真言宗大法欲回传中国,力邀太虚赴日承之,太虚婉辞之。大师之弟子大勇闻之欢喜欲往,他以为“末法众生去圣时远,知见狭劣,垢障丛深。欲令入佛,非得三明六通,难以起大众之信、回俗流之狂,而佛法终无由昌大,劫乱终无由拯救”,而密宗则正可挽此狂澜,为末法众生之良药。于是,他随觉随东渡。太虚大师记之曰:“先则粤之纸密、蜀之大勇,继则有持轮,后则有显荫”。大勇在日本学法甚勤,深得传法者喜爱,后金山穆昭回忆大勇等学密的情况时说:“先年支那有密林、大勇、纯密三法师,殆同时来山修学,是时余当指导之任“。初抵东京,大勇与在东京留学之陈济博同往东密中心道场高野山,辗转访得天德院金山穆昭,并得其许可,传予密法。不久,大勇因学费不足,回国筹措。1923年再次东渡,在高野山密宗大学就学,依金山穆昭传习古义真言宗中院一派教法。约经一年,得四十六世传法灌顶大阿奢黎位(此从空海算起。如按大日如来算起,则为五十三世,一说六十三世或五十一世)。关于大勇之东密成就,太虚大师早有预见,大师说:“考其数人中,于教理素有研究者,只大勇、持松、显荫诸师尔,故真能菏负吾国之密宗复兴之责任者,亦唯其三人尔”。大勇在日本期间,时常与中国佛教教友通信联系,如1921年秋大勇到京听太虚讲经时,曾携法尊同往,法尊之后对太虚大师之武昌佛学院有了很大兴趣,他曾去函大勇恳为引荐,大勇慈悲允为法尊作介绍和保证人,使法尊入了大师之武院。1923年冬,大勇习胎藏、金刚两部大法归,开始了他弘扬东密的事业,他的弘传被后人认为东密畅传中国之始。初抵上海,他即被沪杭佛教信徒江味农、吴璧华等邀请,先在沪开坛,授灌顶多人。次至杭州开坛,传十八道法。据说得一尊供养者十人,从受咒印大方便者多达百人,其中包括潘国纲、王吉樗等政界人物。太虚大师闻大勇归国,传密于杭,即以严切手书责以速来武汉,乘寒假期中传密法。民国十三年即公元1924年1月27日,应太虚大师力约及武汉僧俗之请,大勇南下传法,开坛传密于武院,在武院受到师生们盛大欢迎。在此,大勇先后开坛传法十次,主传东密十八道法,入坛受法灌顶者达二百三十七人,主要是该校学员,还有不少居士,其中如李隐尘、赵南山、孙自平、杨选承、杜汉三、黄子理等社会名流均参加,及女居士十三人。据说,当时武院的学员大都倾心于密宗,武汉密法忽焉大盛。武院之法尊法师亦预会并修学文殊法。法尊说:“在那里第二年冬天,大勇法师回到武昌传十八道,各处的佛教徒无论在家出家,都有唯密是尚的风气。我也给勇法师当过八天的侍者,我也学过十八道和一尊供养”。自1921年与东密结缘至1924年春,是大勇法师修学并弘传东密之经过。
1924年暮春,大勇法师赴北京,在北京投白普仁尊者学藏密,欲贯通日、藏两系密法,建立完全的中土密教,此时也就结束了他弘传东密的活动。此春夏,他在北京与雍和宫白尊者一同闭关于善缘庵,修藏密金光明护摩法,法师便觉得西藏的密法比日本东密来得更完善,如日本密教由中国阿奢黎惠果传予日本弘法大师(东密祖师),而惠果又得自印度阿奢黎金刚智、善无畏,间接又间接;且再日本流传及千余年,中间不无迁变。而西藏密教,则由印度莲花生、阿底峡直接传授,藏地的佛法保持原貌比较好。于是,他便生出深究藏密之心。后来又在京依多杰觉拔上师学藏密,经过一段时间的修习,感到学通藏密非进藏不可,就发了进藏求法的决心。他初衷本想一人独往,或带一两个人,经白尊者及诸位大护法劝请,才开始计划组织一个入藏求法团进藏求法。但冒然入藏,于语言上必有隔碍,会影响学法,为克服语言上困难,故应先召集一班学僧学习藏文,待藏文稍有基础再进藏。这样,在白尊者、多杰上师指导和胡子笏、汤铸新、但恕刚、刘亚休、陶初白等人赞助下,在北京创设藏文学院,招青年比丘学习藏文。此段期间,大勇为学员等事到处奔波,如1924年初夏,在北京传十八道,函法尊到京相间,面商进藏的事,因他对法尊甚为器重。法尊说:“盖自从入五台亲近勇法师之后,勇法师视我,就如他的剃度弟子一般,时时事事没有不照顾我的。他由日本归来,本想在庐山闭关修成就法,他挑中的侍者,我便是第一个”。由于大勇急于赴杭传法,法尊到了北京,商定了进藏计划,大勇便南下,与忍病痛坚持说法的王恩洋居士一起在杭州佛教会讲经。由于武院学僧及职员对大勇甚为敬佩,闻知其藏文学院将成立,其中多数优秀学僧及职员如大刚、密严、超一、观空、善哲等相继追随大勇北上,大勇南下传法后,大刚、法尊等留京筹备,八月间大勇到京准备开学时,又带了朗禅、恒演及几位居士同来。终于,在大勇积极努力及白尊者、多杰上师指导下,又得诸大护法支持,1924年10月11日(农历9月13)在北京慈因寺正式成立了藏文学院并开学,主要学员有法尊、大刚、密严、善哲、朗禅、恒演、超一、观空、法舫及几位居士等,因法尊、观空、法舫等均为太虚创办之武院毕业僧,转而来北京随学,这使白普仁尊者这个主要指导人增色不少,藏文学院的成立,使白尊者法会及多杰上师威名风行南北。
藏文学院主要学藏文,充先生任课,同时请多杰上师为导师授藏密知识,开示朗忍次第及藏地佛教之传承仪轨、习定法、修持浅深、成就过程等。经一年余,基础学法有了些成就,1925年5月,大勇改组藏文学院为留藏学法团,乞太虚开示,大师书偈以示之。同时,学法团制定了详尽的行程规划及办事简章。全团由大勇任团长率领之,下设三个股:总务股、专务股、法务股。大刚任总务股主任,股员为严定(记录)、观空、杜居士(管帐)。超一任专务股主任,下又分三个组,采办伙食组三人:天然、密严、孙居士(管帐)。行李组四人:圆住、会中、密吽、霍居士(登记)。医药组二人:恒照、圆住(兼)。朗禅任法务股主任,下设三个组,悦众组三人:法尊、粟庵、智三。侍者组:法舫(管理图记)、恒演(管钱)。香灯组:恒明。(有关组织及章程等详见(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从大勇法师立志于复兴密教试图融会藏密、东密来建立圆满的内地中华密教,到产生了欲西上康藏求密的学法团,大勇等这次进藏举动,可以说是近代密教复兴运动中一个重大事件,也是整个密教史乃至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壮举,象这样有组织有计划的求法活动,在中国佛教史上还是少见的,因此被后人视为汉僧求法西藏的创始者。
学法团于1925年6月4日从北京出发,一路上又是传法灌顶,又是说皈授戒,热闹极了。火车便是专车,轮船也是包仓,十分风光。先南下武汉、宜昌(严定、会中即在汉口加入学法团),再上重庆,登峨眉山,因时至夏日,便在山上避暑并主持打七,顺便做了个五七息灾法会。秋初下山,在嘉定乌尤寺阅经,说来很巧,年幼的游隆净(即后来隆莲法师)此时正在乐山乌尤寺路边玩,巧遇大勇走过,他那身袈裟使游隆净看了心醉,生出出家之念。据《当代第一比丘尼隆莲法师传》记载:“秋,大勇从日本学成归来,准备赴藏学法,途经乐山,去乌尤寺拜访”。(另据其载,1924年大勇自日归国后,曾到成都少城佛学社讲经)但,该书作者因调查不清故,以至书中时间多有误处,如在书后所附之“隆莲法师生平大事记”中,误以隆莲于1916年见大勇法师于乌尤寺,大勇于1919年夏方出家,何以隆莲在1916年便见到大勇的僧相状了呢!乌尤寺的“乌尤”二字乃梵文音译,为印度密宗瑜伽部主尊之一,寺内现保存唐代铸造的乌尤铜像一座。求法团成员于寺中读了《南海寄归传》,对义净法师赴印度取经甚为钦佩,义净求法诗“去人成百归无十,后者安知前者难。后贤如未谙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更是鼓励他们努力进藏求法。秋末,学法团由嘉定进发雅安,由于一路上有几处匪区,全体分水陆两道进行。自洪雅以西,没有官兵做保障,勇师担心众人被劫,电请军队保护,把他们三十几个人护送过雅安。在雅安休息六七日,赶赴打箭炉,越过大相岭,几经风险才到了康定打箭炉,时值冬末,留居安却寺,进修藏语文。能海上师(俗名龚辑熙,曾与人创办少城佛学社)1925年10月与永光等进藏求法,后在康定与大勇学法团会合,欲共同进藏,但因经费不足,返蓉筹措,后与永光、永楞、永严、常光、登约、太空等再次进藏。1926年春,大勇、法尊、朗禅等上康定跑马山,亲近慈愿大师学习,听讲藏文文法《三十颂》、《转相论》、《异名论》、《一名多义论》、《字书》等关于藏文的书籍,次学黄教佛教著作,如听受《芘刍学处》、《菩萨戒品释》,尤其是听讲了藏传佛教一部重要经典《菩提道次第略论》。经过近一年的进修,成员们藏文水平均有提高,大家继续西进。
1927年春自康定出发,途经艰险,终抵康藏边境甘孜,但在此受到西藏方面阻止,不得已滞留下来。法尊后来回忆这段情节时说:“勇法师是支官差用官兵护着进藏,一路上轰轰烈烈,大有不可一世之概,尤其那沿途的县长、官员等,皆是争先恐后的受皈依、学密咒,郊迎郊送,川边的蛮子们哪里见过这样尊重优礼的盛举呢!也就因为勇法师的气派太大,藏人误以为国家特派的大员,西藏政府来了一纸公文挡驾,并有两张通知甘孜的商人,不准带汉人进藏”。由于中途受阻,只好在当地先寻师求法,而此事变直接影响到了学法团整体的命运,使之未能如前所愿。四五期间,法尊随大勇移住甘孜对河的札迦寺,亲近依止札迦诸古大师及其上首弟子,广学显密教法,尤其钻研密教。尔时有一大德安东格什,学德兼优,映夺全藏,曾依止札迦大师遍学显密,其亦为大勇、大刚、法尊等授白度母、金刚手、四面大黑天等结缘灌顶法。大勇以深厚的密宗根底及雄辩的口才,为各传法上师喜爱,得传法阿奢黎位(传法阿奢黎,亦称传教阿奢黎、传灯阿奢黎,受此法位者,有资格传授密法仪轨等)。于此年中,大勇在甘孜讲《菩提道次第略论》,由胡智湛居士笔记,录成汉文,但当时未讲《止观章》。大勇法师出家十载所遗文著,略有散见,然成书者仅译讲之此《略论》,后得法尊补足《止观》一节。并由严定阅校藏籍,坐空整治笔录,成六卷本。据说,勇师最初的《略论》在成都印行时,一般已经有佛学根底的人,喜爱得简直难以形容。1929年6月,学法团大勇等人,发《劝请全国居士如律地护持三宝书》,于印光(净土宗名人)倡导净土而杂以儒说有所批评。
但是不幸的是,由于法师常年奔波,一心弘法而不注重身体,所以积劳成疾,终于民国十八年即公元1929年秋8月初10日早晨,壮志未酬而示寂于四川甘孜札迦寺,年仅三十七岁,时戒腊十载。大勇法师临圆寂时,还一心想着佛法的弘扬,他未竞事业,因而将法尊叫到面前(勇师最喜爱法尊,有空闲时常为他讲些过去高僧的故事),很殷重地嘱咐法尊,教他去昌都从安东格什学《菩提道次第广论》(此论及前述之《略论》,皆为宗喀巴大师依阿底峡佛尊《菩提道灯论》所著,为道次第中最为全面之论述),学了以后,无论如何还要把它传到内地来。勇法师说,如这部书能够传到内地,连他们进藏学法的三十几人所受施主一切供养,都可消受得了而不白费。其实,勇法师已造下《菩提道次第广论科判》(即《广论》之各科目分章及立名等工作),只不过未能接下传讲全论,因此遗志未了。法尊法师遵遗嘱,去亲近安东格什,学此《广论》,后于1935年冬出版印行(莆田广化寺1991年5月印行本后附录有阿底峡尊者《菩提道灯论》及大勇法师之《广论》科判)。勇师寂后,法尊、恒照、密严、密慧等将其遗体在格陀诸古指导下荼毗,翌年(1930年)春由大刚、密严等迎灵骨回康定起塔。至此,轰轰烈烈的学法团因大勇的示寂而停止了集体活动,其成员或仍留在康习法,或先回内地弘法,或也示寂于当地,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继续进藏求法,如恒演、密悟、法尊、大刚等,而且密悟、恒演留学拉萨得格西学位,法尊受多种灌顶并广学经论。大勇为湖南密吽、湖北密慧、四川密严、河北密悟、密圆之师长,法尊又被法师器重,密悟、法尊二人获成就甚大,足以慰勇师之灵了。但是,以勇师本人来说,因心怀赴拉萨之愿,势必会转世以圆之,次年果然转生康地,灵童是由格鲁派法王甘丹赤巴及颇邦喀大师等选出的,此二人乃藏地黄教佛法之权威,因此勇师之灵童是可信的。勇师灵童由大刚教授之(勇师寂后学法团由大刚率领一段时间),据闻,后又入藏学法去了。勇师的一生虽然短暂,但足以够后学敬仰了,他为佛法尤其是密教所做出的贡献,是可彪炳史册的,他是我们后学者的榜样,如同太虚大师在《菩提道次第略论.序》中之赞曰:“华夏密乘中兴,暨西藏佛法内流,大勇实为前茅”。